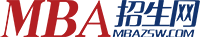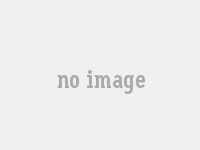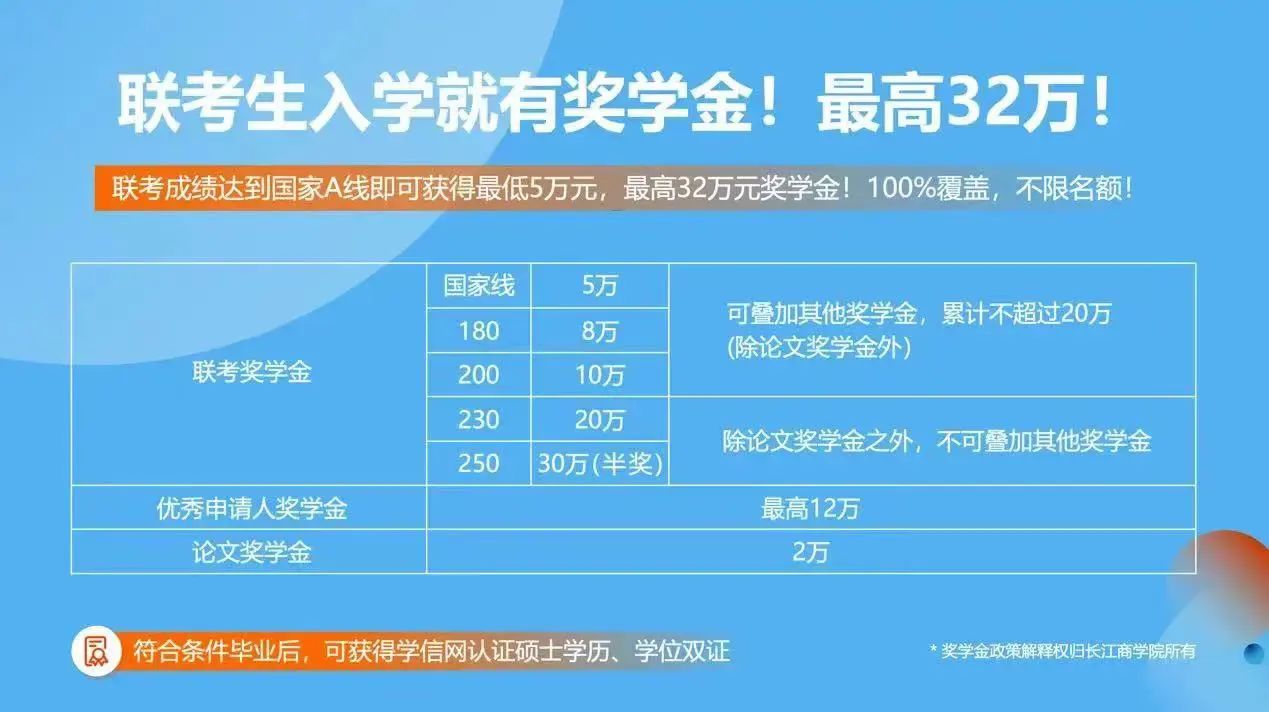調查:考上北大的那些人,后來都怎么樣了?
一個北大學生問老師:“老師,像我們這樣沒有背景的普通北大畢業生,要如何定位自己?”
老師說:“社會底層民眾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那批人。”
我在這個畢業季采訪了幾位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社會底層人民,他們在18歲那年的某次考試中“獲勝”,在這個校園里相聚,他們的驕傲互相碰撞,然后散落向四面八方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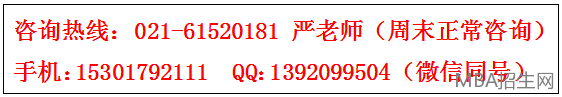
美國有一句諺語:High school never ends. 北大對于學生來說也是如此,那些發生在校園里的事情,會在畢業很多年后,繼續發揮它的長尾效應。
當他們帶著名校的光環踏出園子后,北大這個標簽對于他們來說又意味著什么呢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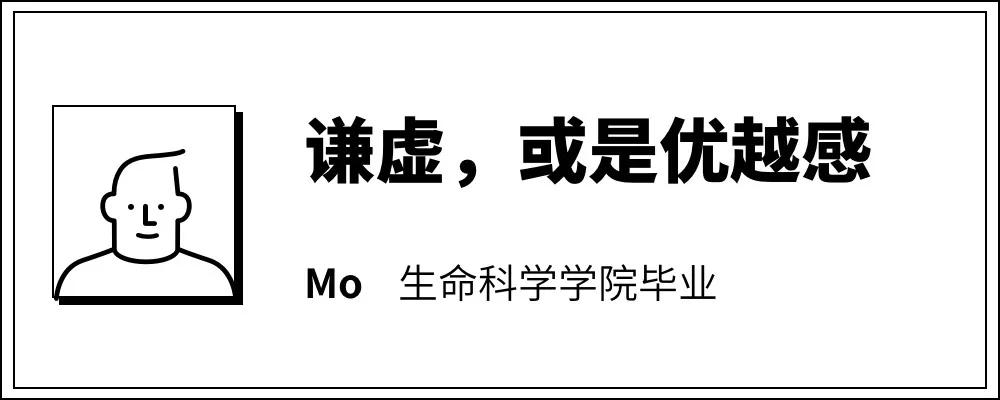
和第一次見面的人聊天,不到萬不得已,我從來不主動說起自己的學校,生怕別人知道,給母校丟人。
就算談到了學歷背景,我也會延遲“北大”二字的出現,以避開后續可能的各種戲劇性的提問。假如別人問我,你在哪里上學? 我會先說,我在北京上學。非得是對方摁著我的頭再問,北京哪個大學?我才會說北京大學,同時眼神閃躲,聲量變小,好像是買的文憑一樣。
如果第一時間說出來,人家會覺得我迫不及待想炫耀,所以少承擔些贊美,免得受那么多戲劇性的大驚小怪和詆毀。
但如果你想謙虛一點,小聲說是北大畢業,對方又會覺得你在裝腔,會想:“你都是北大的了,還說自己不夠優秀,什么意思?這不是寒磣我們剩下的人嗎?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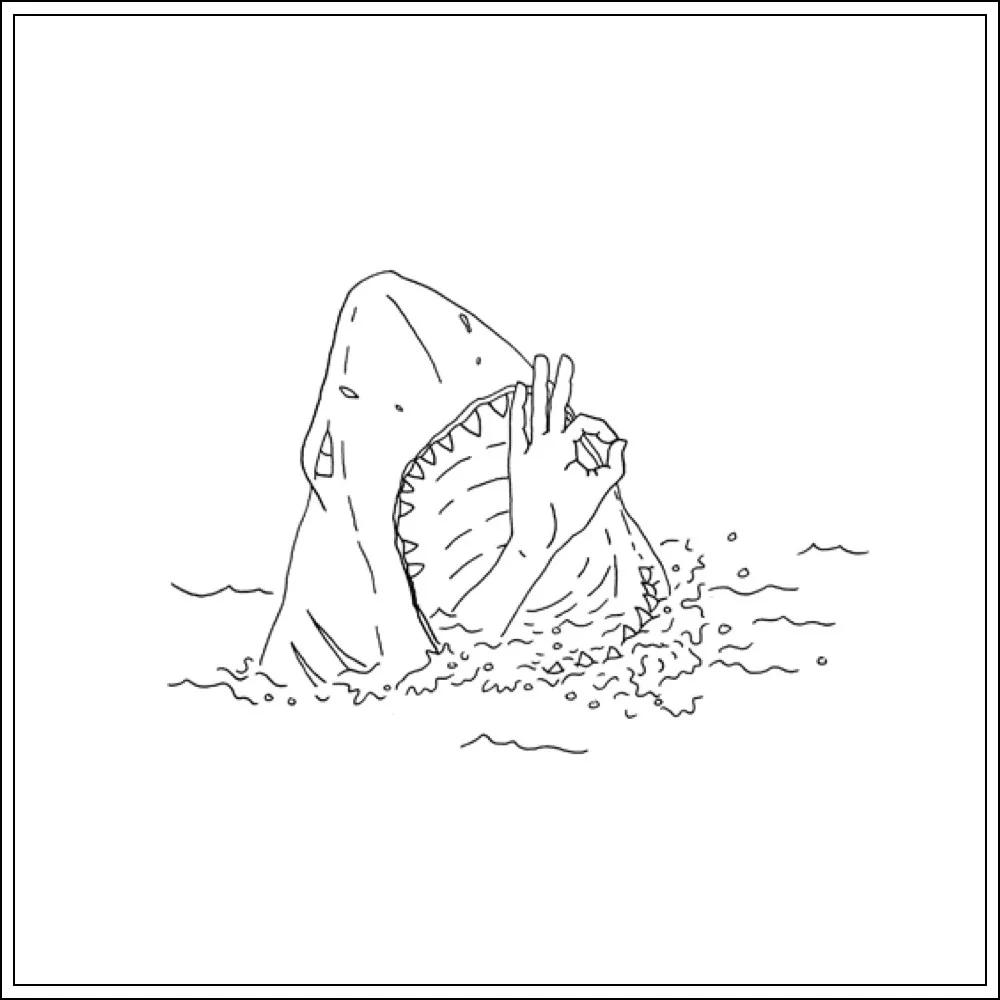
說到底,還是因為我認為自己的實力配不上學校的名聲,所以才不敢大方地向別人介紹自己是北大的。
我和一些校友聊天的時候,經常把“我校”稱為“貴校”,比如:
“你知道么,貴校最近又有人獲獎了。”
“厲害,貴校真厲害。”
本質上是在表達一種疏離感,因為深感“校強我渣”:杰出的北大校友、老師、同學們取得的成就,我等實在是配不上,于是甚至不敢稱之為“敝校”,而稱為“貴校”,讓自己聽起來像個外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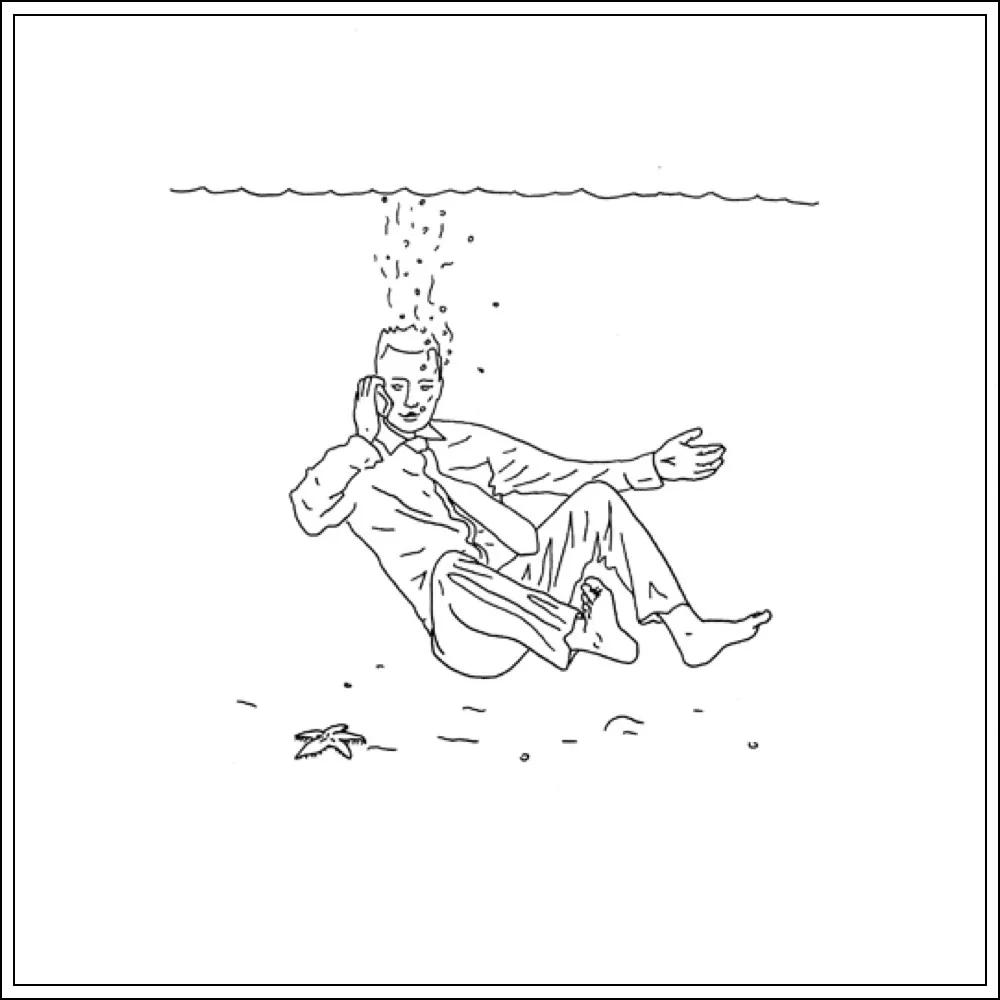
我覺得自己沒有什么優越感。啊,可能只有一個時刻會有,就是我拿著校友卡,從東南門進校園的時候,尤其是碰上清明五一端午這種小長假,會有一堆家長帶孩子排隊來學校參觀。
這時,我就會裝作云淡風輕地掏出卡,沖保安隨意那么晃一下,然后淡定自信地走進校園,腦補旁邊的排隊進校園的社會人員向你行注目禮,那時候覺得挺爽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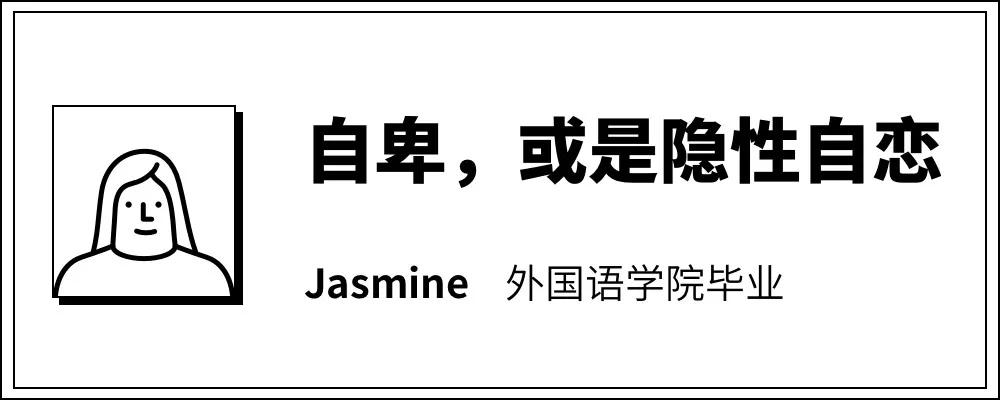
我到學校報道第一天,在宿舍見到了另外三個室友,分別來自山西、河南和江蘇。通過一陣寒暄得知,這個宿舍除了我之外,都是狀元。面對我驚恐的稱贊時,她們連連解釋道:市狀元,不是省狀元,不厲害的不厲害的。
拿到錄取通知書之后,我已經聽過無數詞警告:“雖然你在高中是最厲害的尖子,但在北大,誰不是呢?可千萬不能驕傲啊。” 尤其對于我這樣的北京考生來說,成天受到“400分考北大”的質疑,已經早就認識到自己在高考中占的便宜,也自以為做了足夠多的心理建設,但內心總有一個驕傲的聲音微弱地說:既然我能考上,應該也是有一些本事的吧?
然而事實證明心理建設還是沒到位,開學第一天我就受到了打擊。而這只是個微不足道的開端,后續會有千千萬萬個降維打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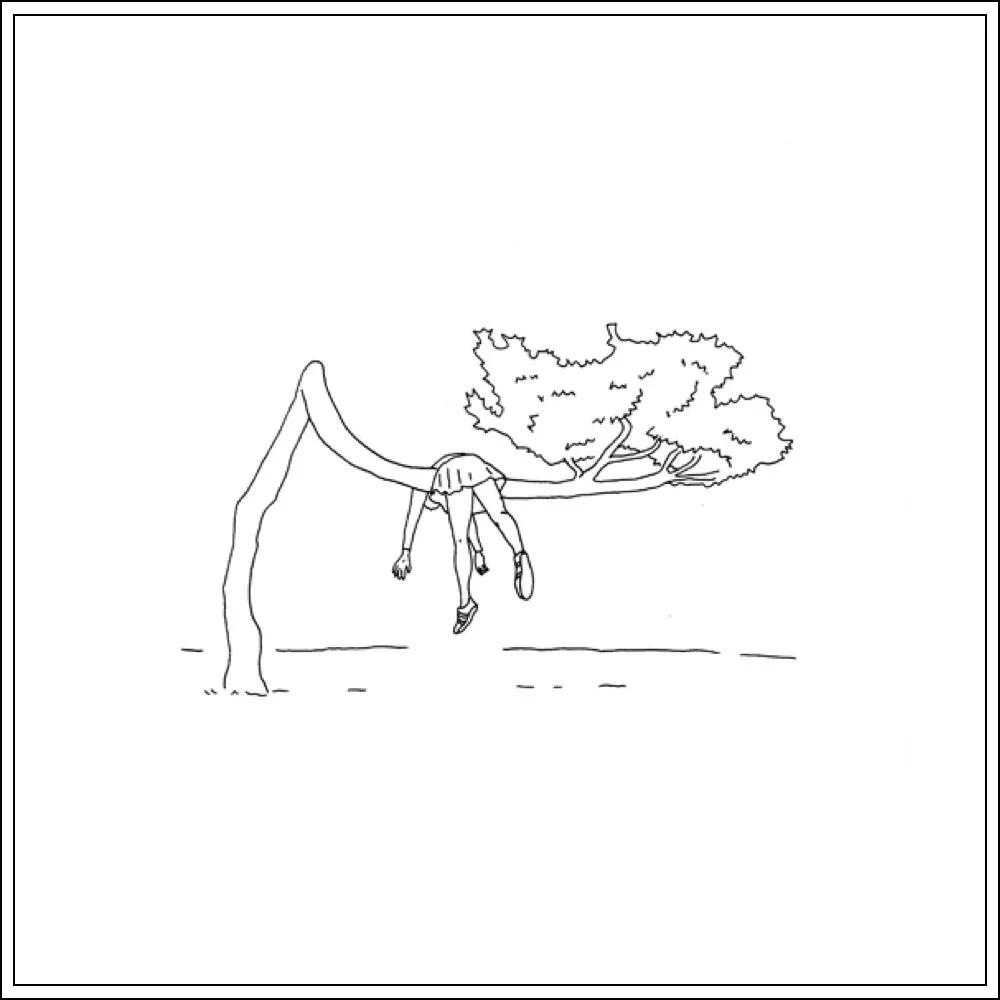
我們學校里曾流傳著一句話:在北大,你不僅能在每個領域中分別找到比自己厲害的那些人,你還能見識到某一個人,TA 在各個方面都比你強。
應該說我的驕傲始于被北大錄取,只維持了一個暑假。取而代之的是落差感和自卑,身邊所有人都在提醒你:你不夠優秀。
這些人真實地出現在你眼前,和你一起上課、一起吃飯、洗澡、睡覺,讓你階段性地產生自我懷疑:我是如何和這些人在同一個校園里的?接下來就會苛責自己:我怎么這么差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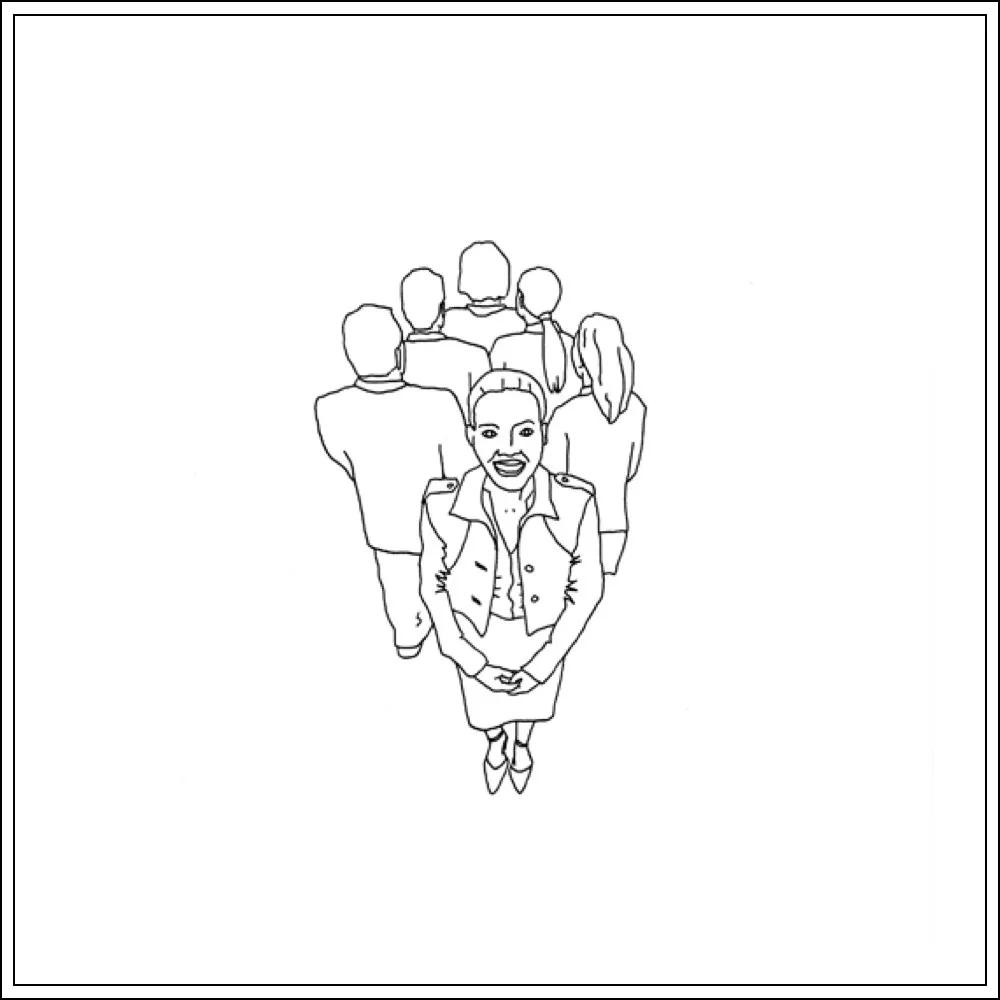
我覺得北大人里面有很多隱性自戀者,他們有著青春期時因為好成績而建立起的自信(甚至自戀),同時,在18到25歲這個三觀養成最關鍵的時期,又處于北大這樣相對特殊的環境中,受到了無數打擊而引發的脆弱、敏感,致使自戀與低自尊在他們身上共存。
這種自戀很特別,比如你看清華的人,整體就比較務實,到哪里都抱團,一個公司里或者在國外同一個學校讀研讀博一定有親密的校友會。而北大人就比較散漫,不屑于抱團,而且通常眼高手低,內心清楚是非對錯,但懶得動也懶得管。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被視為精致的利己主義。
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我校的BBS,不滿會嗶嗶、吐槽,但很少有人去解決、找人溝通。只關注言論自由、程序正義,抒發完觀點之后,后面就不管我的事了。只有自戀的人才會有這種“我就默默地看著你們表演”的狀態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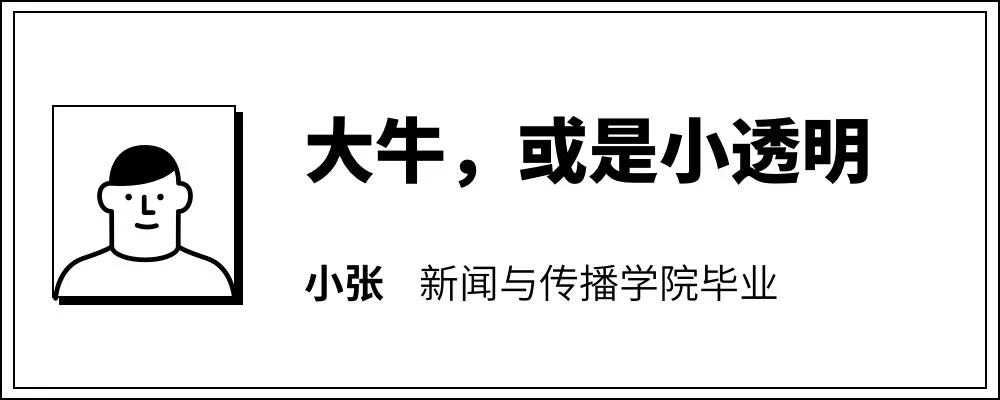
在北大分兩種人,領域大牛和小透明,個別大牛太耀眼了,所以襯得其他人都是透明。大牛認為自己比學校厲害多了,來你這上學是給你增加榮譽的。而像我這樣的小透明,是消耗學校的榮譽的。
每快到畢業季,你到未名 bbs 里的工作或出國版看,一頁接一頁滿眼的 offer 求比較帖子,隨便拿出來幾個崗位/學校,就能嚇死人。我認識的一個師兄,畢業之后考公務員,進了中共中央辦公廳。
過于光鮮亮麗的大牛事跡廣為流傳,讓大眾不可避免地以為,只要是北大畢業的,出來工作肯定非富即貴,怎么著也得去國務院、部委,或者年薪至少幾十萬起。

我老家那些親戚們都是這么認為的,覺著我既然上了北大,就一定也是個人物了,逢年過節一見面兒就讓我給家里弟弟妹妹介紹工作,動不動就來盤問我是不是月薪大好幾萬了。
這種時候我怎么好意思跟人家說,我畢業之后換的倆工作,都是融資不過 B 輪的創業公司呢?就我這工作經歷,跟人家那種一畢業就在大廠里工作的校友相比,基本等同于失業。
當然我也不敢比。畢竟,光是知道有這么厲害的大牛活在身邊,就足以影響你的心態、看事物時的覺知和選擇了。說好聽點,算是一種眼界上的“由奢入儉難”;說難聽點,它更像是一個精神枷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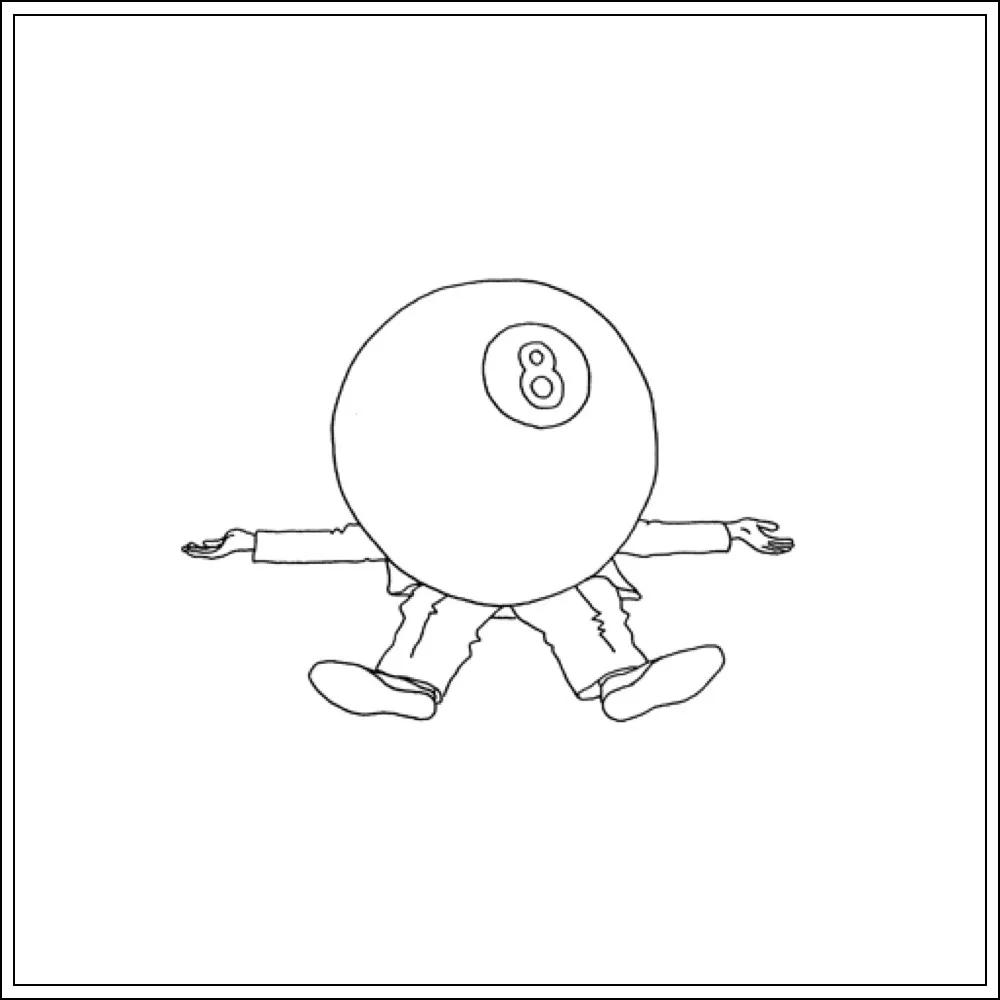
之前網紅李雪琴在采訪中也有提到了北大新聞傳播學院,說了一些“不該說的”,我們院里的老師都氣死了,覺得她“貶低”新聞系。
但我覺得這無可厚非,人家說的確實是大實話,只不過學校里的老師們不能接受畢業的人有混得不好的(更別說李雪琴也不能算是“混得不好的”),好像只要從北大出去,就一定要做到各行各業的頂尖。

我大一的時候曾經聽過一次口譯的講座,只記得那個講師在最后鏗鏘有力地說:不要讓,考上北大,成為你的人生巔峰。
金句出現,嘩啦啦一片掌聲。但我當時隱隱覺得哪里別扭,后來慢慢知道了,覺得別扭是因為,“考上北大”可能真的是我人生巔峰了。從此,一路下坡,勢不可擋。
之前因為抑郁癥去醫院做過檢查,結果顯示我的自主神經系統是極其不穩定的,說白了就是自控力差。看到的那一瞬間我仿佛明白了為什么我考上北大之后就成了學渣,原來是因為生理缺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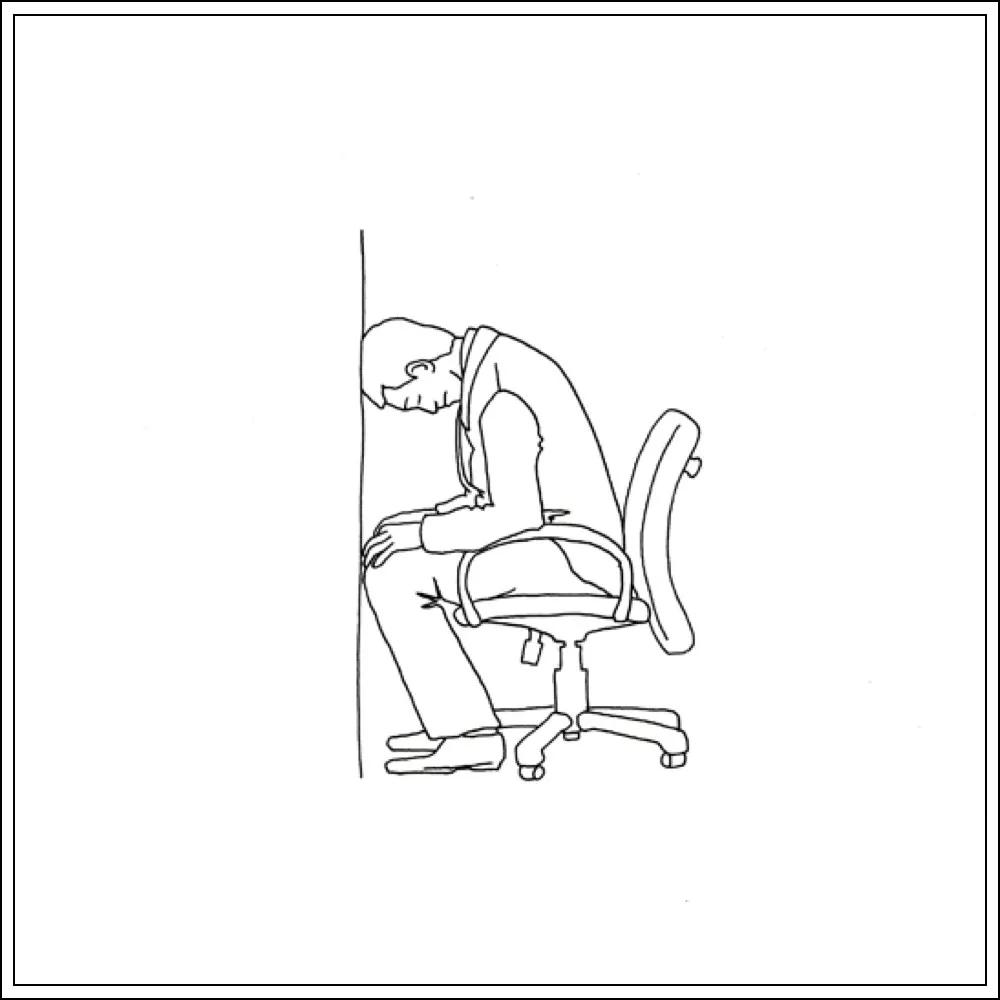
我見過的很多名校學渣都是因為在大學四年里失控,沉迷游戲或者別的,因為分數合格而進入了名校,出去時卻德不配位。
對于我們來說,尷尬的點就在于,在做出更牛的成績之前,身上最顯眼的標簽就只有:北大畢業生。畢業之后如果工作上混的不好,那么這個身份就更是壓力。尤其碰到普通院校或者三本畢業的人還比你厲害的時候,就有種無形的焦慮讓你懷疑人生。

我所在的單位有很多北大畢業生,領導也是北大畢業的,所以對于北大的同事就會顯得更親近一些,聊一些校友之間的話題,但我總覺得對于我這樣表現平庸的學弟來說,無論在什么場合,這樣的話都更像一種諷刺。
雖然心里知道,進了一個學校也不是一樣的人,人與人之間的差異,遠遠大于某個群體與群體外的差異。但一旦你對某個群體產生了歸屬感,就一定伴隨有不切實際的期待:既然我是北大人,那我為什么不能像他們一樣優秀?